倪其心《校勘学大纲》再版
2022/07/26 信息来源: 古典文献学微刊
编辑:安宁 | 责编:知远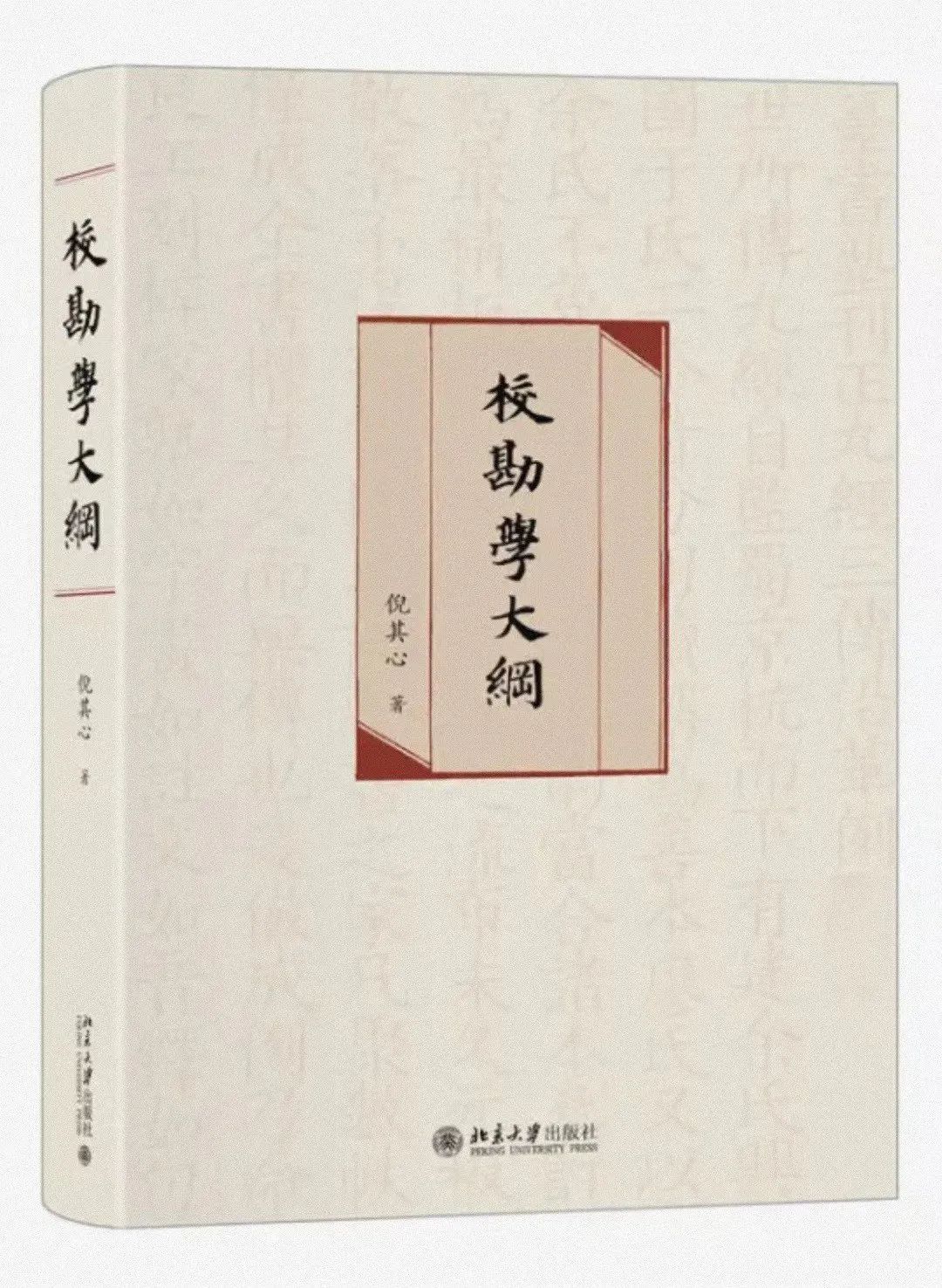
《校勘学大纲》著者:倪其心;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22年4月;页数:416;定价:90.00元
作者简介
倪其心(1934—2002),上海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主任、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古典文学普及研究会副会长等职。主要从事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教学和研究,在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到两宋文学研究及相关文献整理等领域均有精深造诣,为《全宋诗》主编之一,所著有《校勘学大纲》《汉代诗歌新论》等。
内容简介
校勘是古籍的校勘。校勘的本义是比较审定的意思。把一种古籍的不同版本罗列搜集起来,比较它们文字语句的异同之处,审定其中的正误,这就是古籍的校勘。
校勘不是校对。近人常混淆校勘与校对两者之概念。校对是有明确可靠的底本作为依据来判断文本中字词的正误与否;而校勘时则须广罗各个时期各种版本,分析异同,考证语句。校勘与校雠也有区别。校雠一词始于西汉时之刘向,盖独校为“校”,两人对校为“雠”。且校雠还有更深一层意义,即泛指古籍整理工作,可谓包含了版本考证、编撰目录、文字校勘、内容提要等诸多方面,其内涵已经外延至古典文献学领域。校勘相对专精,校雠相对广博。
校勘学是研究古籍校勘的科学,其目的和任务是总结历代学者校勘古籍的经验,研究校勘古籍的法则和规律,为具体进行古籍校勘提供理论指导。校勘学理论是在校勘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具有指导校勘实践的作用,同时又接受校勘实践的检验,并在校勘实践中发展。
就古籍整理而言,校勘学是基础。只有在校勘精当的基础上,我们才可能恢复古籍的原貌,认识不同时期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分析厘清出现差异的原因,并因之更好地认识古籍及当时的学术源流。学习和研究校勘学,自觉掌握和运用校勘的法则和规律,才能更好地进行古籍整理。
《校勘学大纲》是研究中国校勘学的精深之作。本书第一章说明了校勘学研究的对象,第二至第七章论述了校勘和校勘学的历史、校勘学的基本理论、校勘实践的方法和技能,尤其第三章关于古籍的基本构成,发前人所未发,独辟蹊径,从理论和例证两方面解释了中国古代典籍复杂的成因。关于古籍“重叠构成”的看法,颇得顾颉刚“古史层累说”之意。最后一章则辨析了辑佚、辨伪与校勘学的关系。
历代学者通过大量古籍校勘和有关笔记著述,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校勘经验,后代也有一些总结性的著作出现,但大多多例证,少理论总结。《校勘学大纲》则在博采众书之例的基础上,进行了归纳提炼,在根本原则、各类通例和校勘方法上都做了理论性的总结,内容详实全面,可谓“校勘学研究”的里程碑之作。
本书曾于1987年首次出版,2004年修订后再版。本次出版改为繁体,以更适合本书内容。
目录
第一章 校勘学研究古籍的校勘
第一节校勘学研究古籍的校勘第二节校勘不是校对第三节校勘与校雠的区别第四节校勘与校勘学的关系
第二章校勘的历史发展和校勘学的形成建立第一节校勘的发展是校勘学建立的基础第二节先秦有关校勘的记载第三节西汉刘向开创校勘规程第四节汉末郑玄的校勘业绩第五节魏晋校勘的特点第六节南北朝校勘趋向独立第七节唐代不重校勘的倾向第八节宋代校勘向理论发展的趋势第九节元、明的校勘第十节清代校勘学的形成第十一节近代校勘学的建立
第三章古籍的基本构成和校勘学的根本原则第一节古籍的基本构成第二节经典古籍的复杂重叠构成第三节一般古籍的简单重叠构成第四节校勘的根本任务是存真复原第五节忽视基本构成的偏向第六节古籍构成的层次辨析
第四章校勘的一般方法和考证的科学依据第一节校勘的一般方法第二节陈垣的四种校勘方法第三节校勘的考证必须有科学的依据第四节校勘考证的理论依据第五节校勘考证的材料依据
第五章致误原因的分析和校勘通例的归纳第一节分析致误原因、归纳各类通例是校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节疑误和异文第三节误字通例第四节脱文通例第五节衍文通例第六节倒文通例第七节错简通例
第六章校勘实践的具体方法步骤第一节具体校勘前的准备工作第二节了解基本构成和流传情况第三节了解基本内容和结构体例第四节了解基本文体和语言特点第五节搜集他书资料、汲取前人成果第六节对校各本、列出异文、发现疑误第七节分析异文、解决疑误、审定正误
第七章出校的原则和校记的要求第一节系统、扼要、准确的表达校勘成果第二节出校的原则第三节校记的要求第四节改字的处理第五节叙例的撰写
第八章辑佚、辨伪与校勘第一节辑佚、辨伪与校勘的关系第二节辑佚与校勘第三节辨伪与校勘
附录后记“不校校之”与“有所不改” 传承与拓进——读《校雠广义》关于目录、目录学与古籍整理——古籍著录体例、目录学源流、目录分类以及重要古籍目录
序(第二版)日文版前言(摘录)《校勘学大纲》感言
《校勘学大纲》感言
乔秀岩
一
倪老师离开我们已经快二十年了。在三十多年前《校勘学大纲》初版问世的第二年,我在东京才开始进入中国哲学专业,1992年倪老师到东京大学教学,有幸选修倪老师的课。1994年投靠倪老师到北大中文系进修,倪老师跟我说:“来北大读书,可以保证提高你阅读古籍的能力,其他的都不敢保证,也不知道。”当时我只有要读懂《仪礼疏》这一想法,所以倪老师这话简直求之不得。记得当初倪老师跟我约定时间,叫我到空教室,一对一地教我读《仪礼注疏》。因无旁人,倪老师从隔壁教室拿铁簸箕来,放在桌上算临时的烟灰缸,我们两人一边抽烟,一边看贾疏,一句一句解释。当时倪老师就说,如今没有人读经书、学经学,只要有人愿意学,他都感到很高兴,管他是哪国人。真是那样的时代。
后来我写博士论文,倪老师基本上放任,快到截止日期才交稿,倪老师也没叫我修改。毕业回国工作,我自己将博士论文翻成日文出版,辗转听到平山久雄老师看我博士论文后说有倪老师的学风。平山老师是东京大学备受尊敬的一位名师,倪老师在东京的时候,和他私交最深。所以平山老师这一评论让我感到非常愉快。
不知道平山老师的想法如何,我也不敢利用传闻拔高自己,毕竟倪老师是文学,我是经学,基本上不同路,没有可比性。然不管是经学还是文学,研究古代文化的人,往往沉进去跳不出来,全盘接受传统文化的结果,减弱基本的批判能力而不自知。倪老师喜好汉魏南北朝文学,而始终保持最原始的怀疑能力和最洗练的艺术敏感,自然是我所向往的。很遗憾,艺术方面我没有天分,而一直关心学术史,有审思学术方法的习惯,《校勘学大纲》深入透辟的分析,令我感到最舒适称心。
二
学习古典文献需要长期坚持,规诫浮躁之余,往往流于墨守,或以贩卖前辈成说自足,或以罗列信息为学术成果。不仅训诂学、校勘学教材,甚至研究论著,都有以分类罗列为能事者。我们看那种便览式论著,往往感到不如自己看原书为快。然而这种做法颇有传统,如本书第二章介绍王念孙《读书杂志》论《淮南子》文本讹误列举六十二例,后来俞樾《古书疑义举例》、陈垣《校勘学释例》等皆用分类举例之法。可是这些事例的罗列,犹如在晒他们捞到的鱼,我们看了只能赞美叫好,或评头论尾,对我们提高自己的捞鱼能力没有任何帮助。本书第五章介绍“校勘通例的归纳”,是通常所谓“校勘学”的主要内容,而倪老师反复强调“应从疑误的具体实际出发,不能用这些通例去套”,“各类通例的实践意义并不等于客观规律”,“并非普遍法则”,“并非通例”,也就是说无法帮你解决校勘问题。就这一点,足以了解倪老师认真思考的态度。《校勘学大纲》是总结传统“校勘学”的作品,实际上也终结了传统“校勘学”。校勘“通例”只能是幻想,具体情况要具体判断。了解传统“校勘学”是必要的,多接触先人“类例”也不无参考意义,但此外无需过多关心“校勘学”。读完《校勘学大纲》,可以忘掉“校勘学”。只要自己思考校勘何为?该如何校勘?即可。
倪老师对传统文献学成就进行理论分析,探讨其中的本质性问题,其中两点笔者认为特别重要。首先,倪老师注意到,历史上的校勘成果,往往有与今日我们的古籍整理很不一样的目标和意义。如云:“颜师古的处理原则是划一归真,删除繁滥。”“结果便是从疏解出发,而把异文几乎荡涤无遗。”又如《史记正义》《后汉书注》《文选注》等,“撰注的目的是读通读懂”。又如朱熹《韩集考异》“以有无‘神采’‘意象’为判断异文正误的准则”,又如《九经三传沿革例》“主张折中便读”。这些都在说明古代的校勘往往出于一种实用的目的,与今日我们的文献学有本质差别。倪老师对乾嘉时期理校死校之争,也有精准的评论,认为戴段二王“必然不以版本可靠与否为依据,而是以异文为考订对象”。他们不探索那些异文出现的历史情况,追溯最早期的文本,而撇开文本流传的历史,直接思考哪一种文本才“真”。换言之,同样是“存真复原”,在“原”本已经亡逸的情况下,“真”会有不同的标准,他们以符合他们理论的文本为“真”,死校派以历史上存在过的最早文本为“真”。
这也涉及文献的本质复杂性。文字、文本并非客观存在,纸上的墨迹,必须经过主观主体的识读才能成为文本。同样的墨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看,有可能认出不同的文字、文本来。因此,如何认识理解文本,比纸上墨迹更重要。于是本书第三章特别提出“经典古籍的复杂重叠构成”这一概念,说明郑注、孔疏等历代重要的注解,与纸质版本一样体现一种文本,而且比具体一种纸本墨迹更重要。笔者认为,倪老师重视文本的认知主体,在文献学理论上是十分重大的突破。这是第二点。
既然不能排除主观认知,我们究竟如何确定“真”的标准?倪老师告诉我们,这里没有现成的答案,我们要自己去思考。
三
本书第二章回顾校勘学的历史,最后讲到:“最近一些年来,大批专书校注著作问世,大量考古文物出土,以及校勘学专著的陆续出版,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依据,提出了不少的理论观点,形成了良好的趋势。”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半开始,古籍校注专书陆续问世,战国、秦汉的竹简大批出现,尤其重要的是近二十年来通过影印和电子书影的形式,我们能够观察到大量古籍善本,版本研究进展飞快,不得不说我们的资料条件与三十年前有天壤之别。
我还记得倪老师平常用的《文选》是民国缩印的《四部丛刊》影印建本。其实建本据赣州本翻刻,赣州本据明州本翻刻,现在有明州本可用,建本不必去看了。但当时除了影印胡刻本,还真只有《四部丛刊》本(中华书局也有影印)流传。又如本书也有“《毛诗故训传》完整地保存于《毛诗正义》”这种叙述,而《毛诗正义》自然不包含《毛诗故训传》。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要看《毛诗传笺》,确实只有中华书局两大本缩拼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几乎没有别的版本。
1998年,倪老师在看傅刚老师的博士后出站报告,跟我说很有意思。这使我产生要在中国重新影印明州本《文选》的构想,可惜没来得及给倪老师用到。2000年我在东京开始工作之后,有一次回北京,到蓝旗营拜访倪老师。我给倪老师介绍电子版《四库全书》的使用方法,倪老师很高兴。还跟我讲到,以前看像高桥智研究《论语》《孟子》,详细记录每一版本的所有异文,不觉得很可取,但最近越来越感到“死校”是对的。倪老师对《郭店楚简》等也很有兴趣,说抄本的校勘需要另外一套思路。倪老师还没看到古籍数据的信息爆炸,2002年就离开了我们,我们无法就目前的资料条件跟倪老师讨论问题,这让我感到很遗憾。
笔者自2004年开始翻译《正史宋元版之研究》,201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对推动版本学发展算有些贡献。其实,最早是倪老师邀请尾崎康老师到北京讲版本,由陈捷师姐翻译整理成《以正史为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199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不妨说是陈捷和我先后花二十多年的时间,完成了倪老师开头的事业。
笔者与宋红老师合作编过影印明州本《文选》、单疏本《毛诗正义》,与马辛民师兄合作编过影印宋版《仪礼经传通解》、八行本《礼记正义》、南宋官版《尚书正义》《周易正义》,这二十年来相关学者的研究也开展得越来越深入。经张丽娟、顾永新、李霖等学者研究,经书版本的大致情况已经清楚。例如《礼记》,笔者现在阅读郑注孔疏,只看抚州刊经注本与八行注疏本,八行本原则上也只看足利学校的较早印本,不看潘明训旧藏元修本。因为后来诸版本皆未能参考唐代抄本、北宋刻本,所有异文均出后人推论,并不反映北宋以前历史存在过的文本,只要掌握南宋最早的官版,其他诸本无需参考。
四
合理的推论与历史事实之间,有本质的差别。如果说“历史事实”也经过主观认知才能成立的话,我们也不妨考虑不同的客观性程度。从文献学的角度,纯粹客观存在的是各种抄本、版本的原件。拍照影印,有不同程度的失真。文献工作者从事影印,要注意尽量保证影印传真,而对其容有的失真情况,要做充分的说明。这是第一层次。以贾还贾、以孔还孔,是通过文字叙述推论不同文本的过程,大多数情况不会有歧义,但有时也会见仁见智。宋代官版包含不少无意的讹字,一般很容易校正,而有些有争议。尽管做不到完全客观,但通过对每一类文本的深入研究,可以提高准确性和客观性。没有可以泛用的通例,仍能探索具体的规律性,如贾、孔语言习惯等等。这是第二个层次。若说在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宋版还宋版已经完成的基础上,再校勘出一种完美文本,则是一种创造行为。美未必真,而且美有不同的标准。这是第三个层次。
以往学者,包括本书重点介绍的戴、段、二王以至陈奇猷等近人,都在上述第三个层次奋斗,是创造文明的努力。我们现在要历史地研究古典文献,无意于用古籍来创造“文明”,所以我们今日的古籍整理工作要在第一、第二个层次上用力。举一个例子:《檀弓下篇》:“滕成公之丧,使子叔敬叔吊,进书,子服惠伯为介。及郊,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将公事。’”郑注:“敬叔于昭穆,以懿伯为叔父。”孔颖达说:“此后人转写郑注之误,当云‘敬叔于昭穆,以惠伯为叔父’。检勘《世本》,敬叔是桓公七世孙,惠伯是桓公六世孙,则惠伯是敬叔之父六从兄弟,则敬叔呼惠伯为叔父,敬叔呼懿伯为五从祖。”孔颖达根据他的“事实”,认为郑注有转写讹误。若如其说,惠伯向敬叔自称“叔父”,岂不诡异?其实,《世本》以宣公为文公子,而汉人或以宣公为文公弟。文公、宣公为兄弟,则敬叔、惠伯同为桓公六世孙,懿伯既为惠伯叔父,就昭穆而言,敬叔亦可称懿伯为叔父,正如郑注所云。孔颖达未能考虑自己以《世本》为根据掌握的“事实”,并不符合郑玄认知的“事实”的可能性,进而打算改动郑注。如果后人采用孔颖达的主张,直接改动郑注文本,则文公、宣公亲属关系的认定可以统一,同时郑注被架空,不知所云了。我们必须停留在郑、孔不同的“事实”,以郑还郑,以孔还孔,才能保住古代思想文化的丰富性。不能为了拥护一个“事实”,而丢失古人多样的思维和文本。
若要参与点校、校注等整理工作,则先明确整理的目的。只有目的明确,才能判断如何校定最合适。如果目的在提供普及文本,让读者容易理解内容的话,颜师古、《九经三传沿革例》他们的做法也许很合适,尽管那不过是一种文化宣传。我与叶纯芳整理《杨复再修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2011年文哲所出版),连明显的讹字也照录元版,是因为我们的底本是孤本,我们编辑整理,是想在藏书单位不允许影印的情况下,尽量全面体现底本的面貌。部分讹字我们出注说明,是为了不要让读者怀疑是我们的排版错误。又如我与叶纯芳、顾迁老师合作编《孝经孔传述议读本》(2016年崇文书局出版《孝经述议复原研究》附录),《孝经孔传》部分以京大所藏抄本为底本,原则上照录原本。那是因为京大藏本读者在网络上可以直接核对,而且阿部隆一网罗现存诸抄本的校记即以京大藏本为底本。我们的目的在于为学界提供便于研读的出发点,所以认为这样处理最合适。
两年前写过一篇《不校校之的文献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可以算我晚三十年提交的《校勘学大纲》读书报告。我没有上过倪老师的校勘学课程,而《校勘学大纲》是认真学过的。自认为拙文观点是遵照倪老师的思路,继续发展的结果,只可惜已经无法与倪老师讨论。
马辛民师兄给我机会在老师书后面写两句感想,我越想越怀念倪老师,那不是因为他对我有大恩,而是因为他思辨的刚毅正直有永不褪色的魅力。多年来李更师姐一直用《校勘学大纲》教授校勘学课程,培养了众多人才。最后向李更师姐表示衷心的感谢。
原文链接:倪其心《校勘学大纲》再版
转载本网文章请注明出处